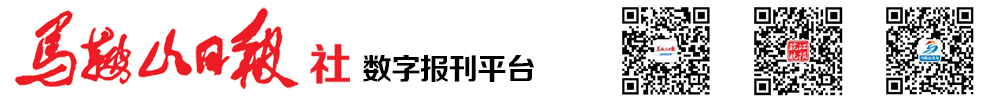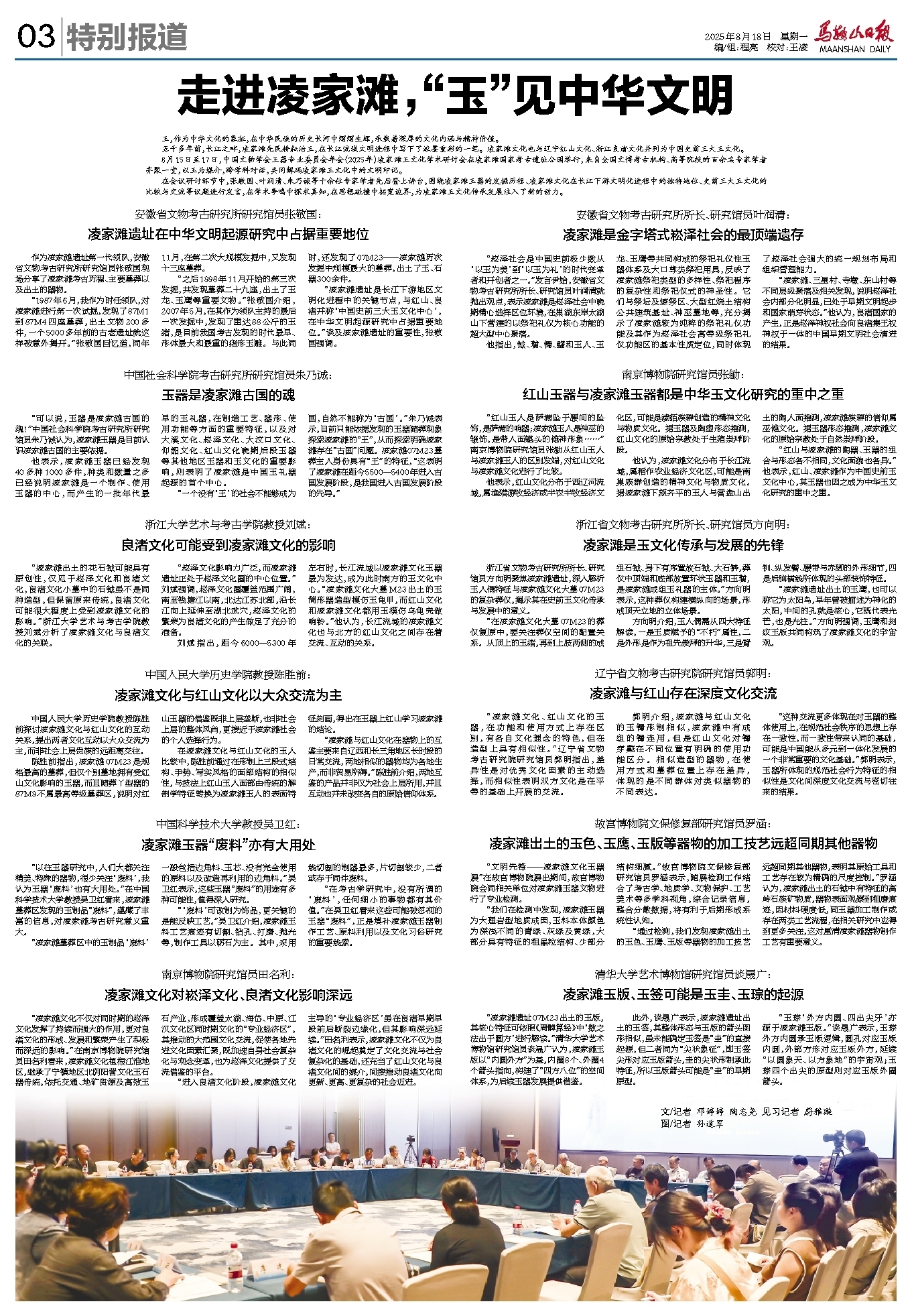走进凌家滩,“玉”见中华文明
玉,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五千多年前,长江之畔,凌家滩先民耕耘治玉,在长江流域文明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凌家滩文化也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
8月15日至17日,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年会(2025年)凌家滩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来自全国文博考古机构、高等院校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玉为媒介,跨学科对话,共同解码凌家滩玉文化中的文明印记。
在会议研讨环节中,张敬国、叶润清、朱乃诚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先后登上讲台,围绕凌家滩玉器的发掘历程、凌家滩文化在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史前三大玉文化的比较与交流等议题进行发言,在学术争鸣中探求真知,在思想碰撞中拓宽边界,为凌家滩玉文化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张敬国:
凌家滩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作为凌家滩遗址第一代领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张敬国现场分享了凌家滩考古历程、主要墓葬以及出土的器物。
“1987年6月,我作为时任领队,对凌家滩进行第一次试掘,发现了87M1到87M4四座墓葬,出土文物200多件,一个5000多年前的古老遗址就这样被意外揭开。”张敬国回忆道,同年11月,在第二次大规模发掘中,又发现十三座墓葬。
“之后1998年11月开始的第三次发掘,共发现墓葬二十九座,出土了玉龙、玉鹰等重要文物。”张敬国介绍,2007年5月,在其作为领队主持的最后一次发掘中,发现了重达88公斤的玉猪,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猪形玉雕。与此同时,还发现了07M23——凌家滩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出土了玉、石器300余件。
“凌家滩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与红山、良渚并称‘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谈及凌家滩遗址的重要性,张敬国强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朱乃诚:
玉器是凌家滩古国的魂
“可以说,玉器是凌家滩古国的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朱乃诚认为,凌家滩玉器是目前认识凌家滩古国的主要依据。
他表示,凌家滩玉器已经发现40多种1000多件,种类和数量之多已经说明凌家滩是一个制作、使用玉器的中心,而产生的一批年代最早的玉礼器,在制造工艺、器形、使用功能等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及对大溪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玉器等其他地区玉器和玉文化的重要影响,则表明了凌家滩是中国玉礼器起源的首个中心。
“一个没有‘王’的社会不能够成为国,自然不能称为‘古国’。”朱乃诚表示,目前只能依据发现的玉器随葬现象探索凌家滩的“王”,从而探索明确凌家滩存在“古国”问题。凌家滩07M23墓葬主人身份具有“王”的特征,“这表明了凌家滩在距今5500—5400年进入古国发展阶段,是我国进入古国发展阶段的先导。”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
良渚文化可能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
“凌家滩出土的花石钺可能具有原创性,仅见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小墓中的石钺虽不是同种造型,但保留原来传统,良渚文化可能很大程度上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分析了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联。
“崧泽文化影响力广泛,而凌家滩遗址正处于崧泽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刘斌强调,崧泽文化圈覆盖范围广阔,南至钱塘江以南,北达江苏北部,沿长江向上延伸至湖北武穴,崧泽文化的繁荣为良渚文化的产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刘斌指出,距今6000—5300年左右时,长江流域以凌家滩文化玉器最为发达,成为此时南方的玉文化中心。“凌家滩文化大墓M23出土的玉筒形器造型模仿玉龟甲,而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都用玉模仿乌龟壳做响铃。”他认为,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也与北方的红山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互动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
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以大众交流为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探讨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互动关系,提出两者文化互动以大众交流为主,而非社会上层贵族的远距离交往。
陈胜前指出,凌家滩07M23是规格最高的墓葬,但仅个别墓地拥有受红山文化影响的玉器,而且随葬丫型器的87M9不属最高等级墓葬区,说明对红山玉器的借鉴既非上层垄断,也非社会上层的整体风尚,更接近于凌家滩社会的个人选择行为。
在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的玉人比较中,陈胜前通过在形制上三段式结构、手势、写实风格的面部结构的相似性,与技法上红山玉人面部由传统的解剖学特征转换为凌家滩玉人的表面特征刻画,得出在玉器上红山学习凌家滩的结论。
“凌家滩与红山文化在器物上的互鉴主要来自辽西和长三角地区长时段的日常交流,两地相似的器物均为各地生产,而非贸易所得。”陈胜前介绍,两地互鉴的产品并非仅为社会上层所用,并且互动也并未改变各自的原始信仰体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吴卫红:
凌家滩玉器“废料”亦有大用处
“以往玉器研究中,人们大都关注精美、特殊的器物,很少关注‘废料’,我认为玉器‘废料’也有大用处。”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吴卫红看来,凌家滩墓葬区发现的玉制品“废料”,蕴藏了丰富的信息,对凌家滩考古研究意义重大。
“凌家滩墓葬区中的玉制品‘废料’一般包括边角料、玉芯、没有完全使用的原料以及改造再利用的边角料。”吴卫红表示,这些玉器“废料”的用途有多种可能性,值得深入研究。
“‘废料’可改制为饰品,更关键的是能反映工艺。”吴卫红介绍,凌家滩玉料工艺痕迹有切割、钻孔、打磨、抛光等,制作工具以砺石为主。其中,采用线切割的制器最多,片切割较少,二者或存于同件废料。
“在考古学研究中,没有所谓的‘废料’,任何细小的事物都有其价值。”在吴卫红看来这些可能被忽视的玉器“废料”,正是填补凌家滩玉器制作工艺、原料利用以及文化习俗研究的重要线索。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田名利:
凌家滩文化对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影响深远
“凌家滩文化不仅对同时期的崧泽文化发挥了持续而强大的作用,更对良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田名利看来,凌家滩文化植根江淮地区,继承了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玉石器传统,依托交通、地矿资源及高效玉石产业,形成覆盖太湖、海岱、中原、江汉文化区同时期文化的“专业经济区”,其推动的大范围文化交流,促使各地先进文化因素汇聚,既加速自身社会复杂化与观念变革,也为崧泽文化提供了交流借鉴的平台。
“进入良渚文化阶段,凌家滩文化主导的‘专业经济区’虽在良渚早期早段前后断裂边缘化,但其影响深远延续。”田名利表示,凌家滩文化不仅为良渚文化的崛起奠定了文化交流与社会复杂化的基础,还充当了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间的媒介,间接推动良渚文化向更新、更高、更复杂的社会迈进。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叶润清:
凌家滩是金字塔式崧泽社会的最顶端遗存
“崧泽社会是中国史前极少数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礼’的时代变革者和开创者之一。”发言伊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叶润清就抛出观点,表示凌家滩是崧泽社会中晚期精心选择区位环境,在巢湖东岸太湖山下营建的以祭祀礼仪为核心功能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他指出,钺、璜、镯、璧和玉人、玉龙、玉鹰等共同构成的祭祀礼仪性玉器体系及大口尊类祭祀用具,反映了凌家滩祭祀类型的多样性、祭祀程序的复杂性和祭祀仪式的神圣性。它们与祭坛及燎祭区、大型红烧土结构公共建筑基址、神巫墓地等,充分揭示了凌家滩较为纯粹的祭祀礼仪功能及其作为崧泽社会高等级祭祀礼仪功能区的基本性质定位,同时体现了崧泽社会强大的统一规划布局和组织管理能力。
“凌家滩、三星村、寺墩、东山村等不同层级聚落及相关发现,说明崧泽社会内部分化明显,已处于早期文明起步和国家萌芽状态。”他认为,良渚国家的产生,正是崧泽神权社会向良渚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的中国早期文明社会演进的结果。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张勄:
红山玉器与凌家滩玉器都是中华玉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
“红山玉人是萨满坠于腰间的坠饰,是萨满的响器;凌家滩玉人是神巫的辍饰,是带人面魌头的傩神形象……”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张勄从红山玉人与凌家滩玉人的区别发端,对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进行了比较。
他表示,红山文化分布于西辽河流域,属渔猎游牧经济或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区,可能是濊貊族群创造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据玉器及陶塑形态推测,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处于生殖崇拜阶段。
他认为,凌家滩文化分布于长江流域,属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可能是南巢族群创造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据凌家滩下颏齐平的玉人与营盘山出土的陶人面推测,凌家滩族群的信仰属巫傩文化。据玉器形态推测,凌家滩文化的原始宗教处于自然崇拜阶段。
“红山与凌家滩的陶器、玉器的组合与形态各不相同,文化面貌也各异。”他表示,红山、凌家滩作为中国史前玉文化中心,其玉器也因之成为中华玉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方向明:
凌家滩是玉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先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方向明聚焦凌家滩遗址,深入解析玉人偶特征与凌家滩文化大墓07M23的复杂葬仪,揭示其在史前玉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意义。
“在凌家滩文化大墓07M23的葬仪复原中,要关注葬仪空间的配置关系。从顶上的玉猪,再到上肢两侧的成组石钺、身下有序置放石钺、大石锛,葬仪中顶端和底部放置环状玉器和玉璜,是凌家滩成组玉礼器的主体。”方向明表示,这种葬仪构建横纵向的场景,形成顶天立地的立体场景。
方向明介绍,玉人偶需从四大特征解读,一是玉质赋予的“不朽”属性,二是外形是作为祖先崇拜的升华,三是臂钏、纵发髻、腰带与赤脚的外形细节,四是后脑横线所体现的头部装饰特征。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也可以称它为太阳鸟,早年曾被描述为神化的太阳,中间的孔就是核心,它既代表光芒,也是光柱。”方向明强调,玉鹰和刻纹玉版共同构筑了凌家滩文化的宇宙观。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
凌家滩与红山存在深度文化交流
“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的玉器,在功能和使用方式上存在区别,有各自文化理念的特色,但在造型上具有相似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指出,差异性是对优秀文化因素的主动选择,而相似性表明双方文化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的交流。
郭明介绍,凌家滩与红山文化的玉镯形制相似,凌家滩中有成组的镯连用,但是红山文化对镯穿戴在不同位置有明确的使用功能区分。相似造型的器物,在使用方式和墓葬位置上存在差异,体现的是不同群体对类似器物的不同表达。
“这种交流更多体现在对玉器的整体使用上,在规范社会秩序的思想上存在一致性,而一致性带来认同的基础,可能是中国能从多元到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郭明表示,玉器所体现的规范社会行为特征的相似性是文化间深度文化交流与密切往来的结果。
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研究馆员罗涵:
凌家滩出土的玉色、玉鹰、玉版等器物的加工技艺远超同期其他器物
“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期间,故宫博物院会同相关单位对凌家滩玉器文物进行了专业检测。
“我们在检测中发现,凌家滩玉器为大理岩型地质成因,玉料本体颜色为深浅不同的青绿、灰绿及黄绿,大部分具有特征的粗晶粒结构、少部分结构细腻。”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研究馆员罗涵表示,随展检测工作结合了考古学、地质学、文物保护、工艺美术等多学科视角,综合记录信息,整合分散数据,将有利于后期形成系统性认知。
“通过检测,我们发现凌家滩出土的玉色、玉鹰、玉版等器物的加工技艺远超同期其他器物,表明其原始工具和工艺存在较为精确的尺度控制。”罗涵认为,凌家滩出土的石钺中有特征的高岭石族矿物质,器物表面观察到粗磨痕迹,因材料硬度低,同玉器加工制作或存在两类工艺流程,在相关研究中应得到更多关注,这对厘清凌家滩器物制作工艺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谈晟广:
凌家滩玉版、玉签可能是玉圭、玉琮的起源
“凌家滩遗址07M23出土的玉版,其核心特征可依照《周髀算经》中‘数之法出于圆方’进行解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谈晟广认为,凌家滩玉版以“内圆外方”为基,内圈8个、外圈4个箭头指向,构建了“四方八位”的空间体系,为后续玉器发展提供借鉴。
此外,谈晟广表示,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签,其整体形态与玉版的箭头图形相似,虽未能确定玉签是“圭”的直接起源,但二者同为“尖状象征”,即玉签尖形对应玉版箭头,圭的尖状形制承此特征,所以玉版箭头可能是“圭”的早期原型。
“玉琮‘外方内圆、四出尖牙’亦源于凌家滩玉版。”谈晟广表示,玉琮外方内圆承玉版逻辑,圆孔对应玉版内圆,外部方形对应玉版外方,延续“以圆象天、以方象地”的宇宙观;玉琮四个出尖的原型则对应玉版外圈箭头。
文/记者 邓婷婷 陶志尧 见习记者 蔚雅璇
图/记者 孙道军